15年重症监护室主任眼中:ICU病房的人文意义

郭应军(中)在抢救病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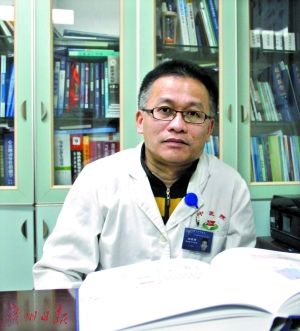
人物简介:郭应军,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、广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。
中山市中医院的郭应军做了近15年ICU病房主任。在ICU病房内外,看过太多生与死,见识过太多悲欢离合。郭应军说,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讲,ICU病房又承担着除去治病救人之外的另外一种意义。
他把ICU病房内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,比喻为“风筝”与“放风筝的人”,无论“风筝线”最终会不会断,但当“放风筝的人”先一步松手时,“风筝”就一定会离他而去,飞向远方。
作为ICU主任,郭应军说,他必须把生死看得很开,否则就会过不了自己这关。他经常会对那些已经是博士甚至博士后毕业的医生说:“在没有经历过临床的磨砺之前,你们都是‘不学无术’的,因为书本上的知识懂得再多,没有经历过临床的救治,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纠葛,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。” 文、图/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
12月28日中午,中山市中医院ICU病房外,手术室门口的“手术通道”被患者家属挤得满满当当。在一旁的家属等待区,疲惫的家属们都打起了瞌睡,有的仰头,有的低头,有的则在冰冷的座位上铺一层纸壳子,睡在了上面。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,无论是怎样的结果,都会给家属们带来情绪上的巨大波动。郭应军告诉记者,有时在抢救结束后,就在这片家属休息区,会传来响彻整栋大楼的哭嚎声。
那是一个生命离去后,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“悲歌”。
医生不能“死”在病人前面
在ICU病房,郭应军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个体生命在生死抉择时对于这个世界的“反馈”。他说,当生命已经无法挽留时,它会一点点消失殆尽,无论怎样用药都无济于事;而当生命对这个世界充满“留恋”与“不舍”时,他也能看到抢救过程中,它在生死线上拼命地挣扎。
他印象最深的那个生命,是一个中山的患者,经历过两次肝脏移植之后,情况急转直下,生命似乎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。“之前抢救的医生都放弃了,因为按道理说的确救不下来了。”
郭应军指了指办公室内棕色发黑的沙发说,那个病人当时的脸色就是这个颜色,“当时患者连小便都没有,每天要从腹部引流出2000多毫升的脓液,多个器官衰竭,也是抱着必死的心,来到ICU试试看。最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抢救恢复,病人最终活过来了”。
“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说,医生绝对不能‘死’在病人的前面。”他解释说,在病人没有真正死亡之前,医生一定要有救活病人的努力,不能先于病人放弃。
“生机是对世界的‘留恋’”
在郭应军的印象中,同样是一个必死之人,他们还是挽救了她的生命。
那是一个生产的孕妇,在生产时羊水栓塞,羊水进入到妇人血液中,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,就造成了产后DIC(即弥散性血管内凝血,指在某些致病因子作用下凝血因子或血小板被激活,大量促凝物质入血,从而引起一个以凝血功能失常为主要特征的病理过程),肝脏、肾脏、呼吸器官等都相继衰竭。
为此,卫生部门还专门组织了多位专家进行会诊,最后的结论是“准备放弃了”。但他还是一步步去做医生该做的事情,对血液进行净化,上呼吸机代替呼吸,希望病人的病情好转,最后患者起死回生。
“看开生死,才能过关”
“生机”是生命对于这个世界的“留恋”,当最终逝去,也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但在ICU当医生,最难回避的,就是死亡,生与死,相依相存。“见过太多的生死,也就必须把生死看得很开,否则医生自己会过不了自己这关。”
据郭应军的估算,在每个月近两百人次的抢救过程中,ICU的死亡比率能够达到10%~20%。“对慢性病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来讲,死亡已经有了一个慢慢去接受的过程,所以相对来说,并不是难以接受。”郭应军说,但还有一部分死者是突然事故死亡的,家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,这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。
对于患者的死亡,作为医生感同身受,“看着病人的家属哭得那么伤心,自己都有掉眼泪的冲动。”
但他也经常会对ICU较年轻的医生说,如果把每个死亡的病人,都归罪于自己,那么医生就很难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,“生老病死”是自然规律,有时人的力量在规律面前,是苍白无力的。
“对未知的恐惧”
在进入到ICU之后的第二年,郭应军就经历了死亡的恐惧。
“那是对未知的恐惧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不知道是什么病。”郭应军说,在2003年1月4日与1月8日,ICU分别来了两个“类似”症状的病人。
两个人都是年轻人,而且都是厨师,他们的症状是相似的。起初只呈现出感冒的症状,但是病情发展迅速,在30多个小时之后,通过胸部X光片可以观察到,原先还只是在肺部呈小范围分布的“石变”部分,迅速扩张到整个肺部。更加令他们束手无策的是,几乎用遍了所有的抗生素,但是全部无效。“用了9种抗生素,理论上存在治疗可能,但是无效。”
随后,两个厨师的家属,以及有过密切接触的人,包括医护人员,都呈现出了类似的症状。后来,病情蔓延开来,这种病被命名为“非典”,而那两个最初出现症状的厨师,则被称为“毒王”。
当时,这两个“毒王”就被安排到郭应军所在的ICU进行救治,在给“毒王”进行插管护理的过程中,郭应军也不幸“中招”。
如今回想起当时的过程,郭应军最关心的仍然是“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”当时,他和另一名感染了“非典”的医护人员被隔离安排在了同一个病房,与他苦苦思索病因相对的是,邻床的医护人员则更多地处理着“身后事”。
“我当时肺部‘石变’的部分最多达到了75%左右,只能依靠四分之一的肺通气。”郭应军说,得了什么病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。
在病情发展到第十五天,邻床的医护人员和他相继出院。到了此时,他才有些后怕地觉得,自己“在鬼门关”上遛了一圈。
“原来病是有自限性的,烧退了就好了。”郭应军说,他清楚地记得出院的那天是年廿八,马上就快过年了。
情与理的矛盾纠葛
作为ICU的主任,他也经常在情与理的纠葛之中,不断煎熬。
特别是在ICU成立的初期,在医保政策还不是特别普及的情况下,郭应军经常会面对这种“情”与“理”的矛盾。
他介绍说,特别是来到广东打工的务工人员,他们本身又没有什么钱,但是病情也非常严重,需要救治,他会选择先救人。但是,同样在救治的过程中,也会催着病人赶紧凑钱,于情已经开始救人,于理也需要他们支付治疗费用。
因为催病人缴纳治疗费用,他还收到过病人的投诉,说他没有医德。病人认为,“撞我的那个人还没给我钱,我就没钱交治疗费”。
他也觉得很无奈,这就像是没有发工资,就去餐馆吃饭,然后不给钱,说没有发工资所以不给钱一样,原本是“一码归一码”的事情,结果却引来了抱怨。
在那时,欠费的事情经常会有发生,“3个月不到就欠了两百多万元”。在现在医保政策普及之后,至少都能够报六七成,欠费的也就少多了。 ICU病房的
无奈与欣喜
在ICU病房,还会碰到一些癌症末期的患者,这也是一部分特别的病人。“从医学的角度来讲,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了,但是从人文的角度来讲,他们还想着在最后时刻见见自己的亲人。”
他介绍说,这部分病人是癌症末期发病之后,生命垂危之际,想要多等三天或几天,“等着见见从国内甚至国外回来的亲人”。
往往在见到了他们想见的亲人之后,他们就可以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讲,ICU病房又承担着除去治病救人之外的另外一种意义。在病房之外,能够看到太多的世间百态,有爱、有恨、有无奈、有欣喜。
在郭应军办公室的书桌上,摆着一本厚厚的专业书籍。他说,医生是一个始终不断在学习的职业,当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之后,才会越发地发现到自己的不足。
他经常会对那些已经是博士甚至博士后毕业的医生说:“在没有经历过临床的磨砺之前,你们都是‘不学无术’的,书本上的知识懂得再多,没有经历过临床的救治,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纠葛,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。”
他告诉记者,ICU病房有30张床位,总共配备的设备差不多2000来万元,每张床光配备的设备就要100来万元,尽管自己已经在ICU病房当了近15年的主任,但是,他仍然不敢说能够把这100来万元的设备用得最好、最对,发挥最大的价值,“如果没有不断地学习,ICU病房的医生是很难胜任的。”
 人民健康APP
人民健康APP 人民好医生APP
人民好医生APP
热门点击排行榜
联系我们
|
人民健康网微信
微信号:rmwjkpd 公众号:人民网健康 |
人民健康网微博
微博昵称: 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 |
|
电话:010-65367951 邮箱:health@people.cn | |



